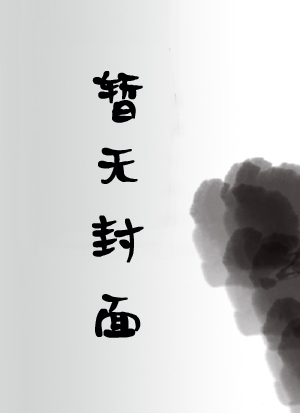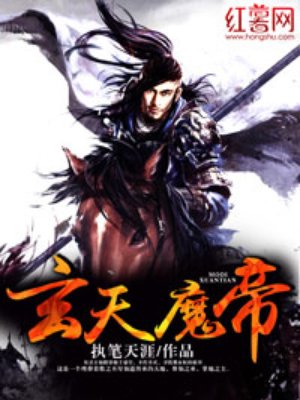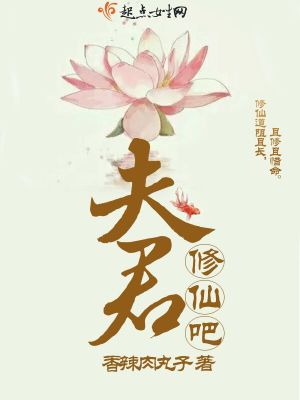第34章
这个题目,是湛秋想出来的主意。**.更新快**诗人湛秋,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,莫过于他那潇洒的,好像从来不甘受羁束的,永远是蓬松着的头发。那是挺性格化的,能够体会到他那无拘无束的,我行我素的内心状态。我们见面很少,联系不多,但他出了这个题目,使我对他刮目相看,原来,诗人不见得都是天马行空的,同样是很现实的,很面对的,很老百姓的,关心着大家都关心的事。浪漫到九霄云外,浮想连翩以后,也能够回到尘世的生活中来,油米酱醋,芝麻绿豆,生活琐事,酒后牢骚,谈些极实际,极一般,极大众化的话题,也不很好?
要是过去,也许就婉谢了,不过,这时的湛秋打来电话约稿,我自然要欣然领命的。
俗话讲,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,这些维持生计的消费,虽然随着物价的上涨,也是一份不轻的负担,但怎么花,总属有限。舍此以外,高和低的差幅就大了,于是,就产生了高消费的种种说法。
虽然,高消费离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,还很远。何以为高,何以为低,也无定论。但人是消费动物,看人家购物,大包小裹,钱如流水,你阮囊羞涩,捉襟见肘,难免汗颜,由不得不生一点儿闷气,慨叹一番高消费的如何弄得人意乱情迷,什么为富不仁啦,什么世风日下啦,就全来了。其实,别人花钱,愿意怎么花,纯系个人私事,本不该置喙。但中国人多,便有各式各样的赞成和反对的看法,也是不以为奇的。
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有的出于忧国忧民的角度,如此消费下去,该怎么得了;有的考虑到我们民族的勤俭传统,不应养成铺张的社会风气;有的建议导向这些大把花钱的富人,更要注意提高自己的精神世界;心武不就写了篇文章,叫做《精神不贵族》吗?有的则痛心疾首,认为追求淫奢侈糜是全面堕落的开始;有的怀着那种吃不着葡萄,便说葡萄酸的狐狸情结,在嫉妒怨恨;当然也有的是在某种失落感下的生气眼红,金钱压倒了曾经有过的优势。看到那些过去根本不在话下的角色,居然也神气活现了,“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,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”,自然不会很开心的。
历史,从来就是这样一浪推过一浪的,“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”,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。
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属于眼红的那一类,不过,诗人带了这个头,也就接着凑个热闹了。
有一天,来了个朋友,告诉我一件事。一位大款,住进了北京昆仑饭店的总统包房。第二天早餐,他点了一份最贵的餐饮。侍者送来以后,他把煎蛋吃了,饮料喝了,但那碟鱼子酱,只尝了两口,就放下筷子,然后结账走了。他在讲到那一碟鱼子酱的价钱为一百九十元外汇券时,面部表情颇为复杂,更甭说那好几千元的住房费了。
我问:“他真付了钱没有呢?”
我的朋友说:“他不付钱,大概不行。”那么,钱是肯定付过的了,而且付的不是外汇券,就是美元。
据说这位大款,是位个体户,虽然有钱,但还未挤进权势阶层。“王侯将相,宁有种乎”,也许将来会有这一天,但眼下不是。所以,他不具备享受免费的资格,自然乖乖付账。话说回来,开饭店本是为了赢利,设总统包房,就得有人来住。如果没有红头文件规定,非总统不能住总统包房,那么谁付了钱,谁就可以过一下总统包房的瘾。继而一想,一个人,周末打一顿牙祭,偶尔下一次馆子,到高级商店买件名牌服装,打“的”而不挤公共汽车,允许自己奢侈一下,用的是自己劳动的报酬,是不算什么过失的。那么此公赚了足够的钞票,想尝试一下五星级饭店的新鲜,或者,想找到一点能住进总统包房的那种人才会有的感觉,好像也无可厚非的。穷莫穷过杨白劳了,都到了卖儿卖女的程度,年三十,还要包顿玉米面饺子呢!
我的朋友直摇头。
“看你这副尊容,很是不以为然的了?”我问。
“他可不是杨白劳!”
“按那标准要求,我们如今的衣食住行,无一不算是高消费了。”
人,为消费而生,这话说得未免有点过分,但,人,生而消费,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。从呱呱坠地开始,一直到进火葬场为止,人,一方面创造财富,一方面也消耗财富。因此,说消费是人的一份权利,他挣他花,他多挣多花,他哪怕没钱借钱花,他人是无权指责,更不能干预的。同样,不消费或少消费,也是人的一份权利,你多挣少花,你只挣不花,你拼命攒钱,一个铜板捏出四两汗来,那也是自我选择的结果,别人也无任何理由说长道短。但我想,花钱的别笑话不花钱的,不花钱的,也别嫉恨花钱的,自尊和尊重别人,是同等重要的品德。
中国人的一个最大的优点,就是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,这是一个很值得为之自豪的传统。西方有老年人孤独地死在自己家里无人过问的事,说明人情很薄,中国几乎很少发生过,主要就在这种你欢迎也好,不欢迎也好的“关心”上了。于是,整个社会像不沉的湖一样,保证你不会被人遗忘,甚至“一方有难,八方相助”,就是由于有这种“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”的互相关心的风气。不过,什么事情都不宜过头,哪怕是好事,过了头,也会走向反面。关心和爱管闲事;和干预人家的私生活,乃至隐私;和动不动就要强行谆谆教诲,而且诲人不倦;和什么迷途知返啊,苦口婆心啊的帮助挽救,绝对不是同一回事。对别人花自己的钱,也要说三道四,就是关心过火的表现了。有些人,总耐不住地要当上帝,妄图指点迷津。当不了上帝,起码也得当个业余警察,有权管你。
其实,上帝把伊甸园装点得多美啊!虽然按他的心愿,造了一个男人以后,还造了一个女人,但是那个男人爬上树去摘苹果给那个女人以后,这大概是人类最早的消费欲望吧?他有点儿失望了。不过,也并没有跟亚当,夏娃过不去,一定要他们改邪归正,回头是岸,写份检查之类,而是由他们自己去生男育女了。苦也是你们,乐也是你们,他不再干预他们的行动,不再指导他们的思想了。
看来,真正的上帝够豁达的,想得开。怕就怕那些冒充上帝的人,和患有指导癖的人。
我们身边的这些冒牌上帝或业余警察,总是看什么都别扭,包括人家花自己的钱,花多少,花在什么地方,也要把眉头皱起来。因此,在他们看来,无非像《击壤歌》里那些葛天氏之民,过着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”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生活,才是最佳境界。没有生猛海鲜,没有时装表演,没有法拉利跑车,没有五星级饭店。只要一片树叶,能够遮住羞处,就足够了。这种彻底的返璞归真,我想即使对那些情不自禁要管人的人,也未必会有多大吸引力的。
因为一个不消费的社会,肯定是没有什么生气可言的。
所以,消费,固然是人的一种欲望,但也更是需要,第一,是人的生存需要;第二,是社会的发展需要。正是消费欲望,催生着创造财富的动力。有买才有卖,物质生产是在人的过好日子的愿望,丰衣足食的愿望,享乐的愿望,舒适的愿望,渴望友谊交流的愿望,探知这个世界乃至宇宙的愿望推动下,才无比地丰盛起来。你想拥有一台彩电,你想拥有一台冰箱,于是有了彩电工厂,冰箱工厂。你想登上月球,遂有阿波罗火箭飞向太空的壮举。
现在我们所谈的消费,强烈也罢,淡薄也罢,都是超越了人类最简单的生存需要以外的事。譬如说吧,中国出现彩电和冰箱,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普及的。在此之前,没有这两大电器,有自行车,缝纫机,手表和收音机的中国人,也照样活得蛮开心的。但是让这些人放弃彩电冰箱,再回到所谓“三转一响”的时代,恐怕就要噘嘴了。所以,正是这种无止境的,好了还要好,再好也不怕好的消费欲望,促进了人类的进展。
大家都知道,猩猩是我们人类的远亲,在动物园里过着有吃有喝的舒适生活,那是人类替它创造的。在它故乡婆罗洲低地沼泽森林和苏门答腊,猩猩的消费欲望,就是雨林里有它随手可摘的果子,此生足矣!所以,不止于只求温饱,温饱之后,还要追求享受,这也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地方。于是,人类从洞穴里走出来,有巢氏盖房,燧人氏取火,神农氏种谷,女娲氏织布,这都在有了消费欲望之后出现的。同属灵长类的猩猩不具备这种要求,至今还在热带雨林里的树干上,懒洋洋地躺着。
不消费,就不会有发展和进步。
如果我们当真地实行一件衣服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政策,那就无需乎动员广大农民种棉花,目前的纺织厂,服装厂,化纤厂可以精简掉一大半工人。我就不能设想这样一来,国家失去了大批税利收入,姑且勿论,对我们失业的工农大众究竟有多大好处?整个国民经济停滞下来,那后果又如何呢?
反对消费,抑制消费,甚至把消费和罪恶相等同,认为凡消费都在暴殄天物似的。这种情绪,多少带有一点儿农业社会的特征,是小农经济思想的反映。因为,我们这个农业大国,数千年来,都维持着自耕农式的简单再生产,人工投入极大,土地产出有限,所创造的财富,极其可怜,好年景也只够勉强糊嘴。“靠天吃饭”,最怕无可防御的灾害袭击。所以,“养儿防老,积谷防饥”,备荒渡荒,免于冻馁之虞,就成了农民一生中的大事。由此所形成的小农经济思想,其中有一条,就是少消费,或者最好不消费。
如果,在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上,对高消费持非议态度,那么,现在城市里大家都在孜孜以求的物质上的一切,好像都要划在被批评的尺度之内了。至于花了数千元去住一夜总统包房的老兄,那不用说,更是要让人痛加谴责的了。
不过,我还是认为,在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情况下,也包括虽然负债,可具有偿还的信用程度,消费是属于一个人的正常行为。我对我的朋友说:“不管怎么样说,这位个体户掏了钱去住,总比那些不掏钱也去住,或者用公家支票去住,慷国家之慨的人,要强得多吧?”
他“哼”了一声,仍不能释然于怀。接着讥诮地说:“难得,难得,这可算是新鲜事物了!”
“你老人家的意思,他是不配住?那么请问,谁是天生的龙种,应该去享受呢?您这样说,不是又多了一层封建色彩了?”
几天以后,我的这位朋友又跑来讲另外一个故事,这回不是北京的昆仑饭店了,而是在上海的南京路上。
一个出租车司机,载着一位大款和一个妞儿兜风。在车里,女的对男的说:“听说有一种永不磨损型的进口手表,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如广告里宣传的那样。”那男的财大气粗,可能多喝了两杯,就对司机说:“拉我们到南京路上最大的钟表店去,买一块试它一试。”这还不容易,到了那儿,二话没说,现掏了八千块人民币,扔在柜台上,买了这块名牌表。走出店门,就在人行道上,进行这次测验性能的游戏。女的先往地上扔,男的也接着用力摔,司机在一旁亲眼目睹。果然名不虚传,硬是不破不损,照走不误。男的急了,对司机说:“放在车子底下,开过去压压看,看它坏不坏?”司机有点儿犹豫,不敢踩油门。男的嘲笑他:“我花钱,我愿意,你怕个屁!”
“结果呢?”我问。
“车子压着表,开过去了!”
“我想不会再不磨损了!”
“成了一块铁饼!”他讲完这个故事,问我,“怎么样?你说——”
“闻所未闻!”
“你没有一点儿看法?”
我知道他耿耿于怀上回的谈话,但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。因为正常消费,和无意义的浪费,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。而且,即或是消费,什么叫高消费,什么叫不高的消费,是比较含混的一个概念。多少钱叫高消费,多少钱又叫不高的消费,从来也没见过,也不可能有的一种标准。因人而异,因地而异,在人均收入为百元的地区,消费百元,和在人均收入为千元的地区,消费百元,在消费水准上,是不一样的。假如在人均收入为十元的地区,那当然是极个别的了,消费百元的话,其分量不会比住总统包房的低。为此,笼统一句“高消费”,抹杀一切消费,我想,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,商品经济,也许不是什么好事。因此,我只好无可奉告了。
他看着我,我看着他。
半天,他冒出一句:“这回你没话了吧?”
他摇头,我也跟着他摇头。
当然啰,他摇我的头,我是明白的;但我摇他的头,他能明白吗?